
不要去控制孩子,往长远了看,孩子人生中很多关键的选择,其实是父母左右不了的。
每年海淀小升初,网络上焦灼的气氛都特别浓。
因为除了电脑随机派位,俗称“海淀六小强”的六所著名中学初中部,都会有一定的“点招”名额,给学校想要招揽的“牛娃”打去“密电”,将尖子生收入麾下。
家长为了孩子能进入重点中学“掐尖”的视野,劳心劳力。最后的结果,也难免几家欢乐几家愁——入选的终究是少数,陪跑的总是更多。
表面上看,“奥数”被禁多年,现实里,主流传言依然在说:重点中学最青睐的尖子生,是各种奥数杯赛金奖、银奖得主。
之前600w粉丝的大UP主+恐龙专家邢立达发微博,“哭诉”儿子小恐龙三年区三好,但因为没有杯赛成绩,一直没接到点招密电。

小红书上有博主搬运了邢立达的微博,底下的留言更像一场久远的PTSD(创伤后应激障碍),曾经的海淀小升初亲历者、幸存者们说:

是的,在海淀,重点中学通过奥数成绩选拔学生已经持续了30年。
第一代“鸡娃”生于1980年代初,是我的同龄人。
他们中的许多,现在也已为人父母。
这是一个无止尽的轮回吗?还是,亲历者已经不想再让自己的孩子重复那个故事?
我采访了我的好朋友小巫。她从小生长在海淀,小学就读于中关村三小,初中被人大附中点招进实验班,高中也在人大附中。
我们相识的那年,我在人大读大一,她刚刚高三毕业,正是进入大学前的暑假。后来我们都经历了一段叛逆的青春。
她对自己的中学时代,自己的母校,一直有一种批判的眼光,这是2000年夏天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能感受到的。
那时我完全想不到,有一天我会写下她的升学故事,一个为了小升初,上8个奥数班的故事。一个从乖巧到叛逆,再到平复、自愈的故事。
以下是小巫的口述。
一、通过3000人选拔
我正式开始了奥数培训班之路
我上小学是1980年代末、1990年代初。那时候中关村三小还不像现在这么“精英子弟”,就读的学生有中科院科研人员的子女,也有单位司机、会计、普通员工的子女。还有学校周边居民的孩子,一部分花赞助费就读的孩子。
我们班同学里,有一个家长是在双榆树菜市场卖菜的,还批发冰棍;还有一个同学家里是外地的,父母在北京做裁缝,专做旗袍,手艺很好,听说给三小的校长、人大附中的校长都做过衣服。
大概是小学三年级时,人大附中搞了一次选拔,班里推选排名前三的小孩去考试。通过考试,就可以进入人大附中办的华罗庚奥校——这可能是北京最早的小学生奥数培训班。
那场选拔考试我印象挺深,我第一次进到人大附中的教学楼里,桌子很高,我坐在那儿,脑袋都快到桌面了,就这么做题。给了一沓不可能有人做完的试卷,至少10页纸,特别厚,你就哐哐往后做。
后来我爸妈告诉我,一共有3000个小孩考试,选了70个人,分成2个班,每个班35个人。我就是其中一个。
于是从四年级上学期开始,我每周日就要去人大附中上华罗庚奥校。这也是我小学时代第一个校外的课外班。如果学得好,初中就可以直接升入人大附中。
印象里,我是华罗庚奥校第二届的学生,上面还有一届。当时这个奥数班是跟人大附中紧密关联的,可以说,是人大附中开启了全北京小学生奥数培训的热潮。
也是从这时开始,奥数成绩变成海淀区重点中学“掐尖”的核心指标。

奥校两个班一开始是差不多的,不久后就分成A班和B班,又继续招进来一个C班。各班开始搞末位淘汰,每次考核之后,从A班选取不一定数量的人降到B班,B班选取最头部的人升到A班,B班和C班之间也是这样。
后来好像又有了一个D班,越来越多比较普通的小孩也被收进来。
我当时的成绩就在B班、C班之间徘徊,好的时候在B班,差的时候掉到C班。
二、为了进重点中学
我妈带我上了8个奥数班
当时北京的小升初已经实行片区内随机分配学校了,但很多好一点的中学都可以提前点招。
点招依据的是什么呢?
跟现在很像,主要是奥数比赛成绩、三好、体育特长、艺术特长什么的。
到了我读五年级,海淀区很多中学都跟风人大附中,办起了面向小学生的奥数班。
核心目的就是:你要是中学想上我这个学校,你就先来报我的奥数班,反正我周末教室也空着,这样我既收了家长的钱,又能考几次试,筛出一批优质的学生,留在我们学校,何乐而不为呢?
家长为了让孩子提早一点有个出路,也不会放弃这些机会。
那时候已经有了最早的“鸡娃家长”。星期天我上华罗庚奥校,我妈在学校花园等我,总听到几个消息灵通的家长相互交换信息:哪个学校又新开了什么班,哪里又有选拔考试怎么报名,各处师资怎么样……
其他家长站在一边,假装不动声色,其实耳朵都拼命伸长了去听。
我妈担心我不能顺利进入人大附中,就想再多几个学校保底,五年级一下给我报了8个奥数班……
等于每个目标学校的“坑班”都占上了。
除了星期天在人大附中的华罗庚奥校,中关村三小自己课后的奥数班,还有:
八一学校一个,
中关村中学一个,
101中学一个,
北大附中一个,
清华附中一个,
海淀教师进修学校一个。
有的就叫奥数班,有的叫超常智力培训班,有的叫什么数学训练班。都要通过考试才能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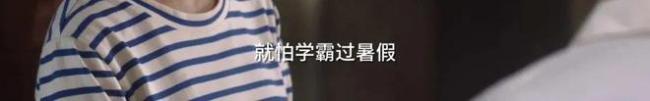
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那个,是平时晚上的。小学大概三点多放学,有两天要上三小自己的奥数班,上完大概是5:30。我妈接了我以后,出门简单吃点东西,就得骑车送我去海淀教师进修学校,好像也是一周两次。
周末的时间能分成几块,在不同奥数班之间穿梭,回家还要做作业。
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委屈,因为我根本就没时间玩儿。我妈也特辛苦,特焦虑。
你想想看,周末一整天一整天的上课,经常是家长给带一点简单的面包、煮鸡蛋,你课间就啃一口,吃完了立刻就得回去接着上课。也没有保温杯,上课不能喝水,只能家长在外面准备着水,怕你渴。
后来我妈终于发现这种状况不可持续,就放弃了几个班。101因为离我家最远,是最先放弃的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那个讲得特别难,跟天书一样,后来也不去了。
我最密集上课外班就是五年级。五、六年级也去考了各种奥数杯赛,迎春杯、智慧杯、还有一个什么杯,我想不起来了。
迎春杯是市里的,智慧杯是海淀区的,都有一定的选拔意味。
只要你发挥正常,基本上能看出来你在海淀区的奥数成绩能排多少名。智慧杯我好像得了二等奖还是三等奖,迎春杯也是。
然后我就被人大附中点招了。其他奥数班都不用去上了。
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五年级那会儿,人大附中做过一次动员大会,礼堂黑压压全是人,可能是华罗庚奥校上下三届的孩子和家长。一位校领导当时拿着扩音器,抑扬顿挫地说:“我现在就把话撂这儿,如果谁要是同时上四中的培训班,恕我们人大附中永不接待!”
现在回想,应该是四中也办了班,在争抢人大附的生源。
三、进入实验班成为“怪物”
没信心说“我是一个挺不错的人”
我们这拨人进人大附以后,直接被编到初中的实验班,分数最高的在9班,是数学实验班,稍微差一点点的在8班,是英语实验班。剩下那几个班,不管以什么形式招上来的,都是普通班。
我们8班的人,本质上都是奥数特长招进去的,但是我们成绩差一点,不配称自己为奥数特长班,所以只能叫英语实验班。
一个实验班大概五十几个人,两个班就一百多个孩子。我们的教室都被安排在走廊的尽头,靠边角的地方,普通班的同学玩的时候绝对不会到我们这边来,就好像有一种隐形的分隔线。
前一阵我们小学同学聚会,有三个初中进了人大附普通班的同学说:我好像从来没有在楼道里见过你。
他们说:我们都不敢去那块儿,因为感觉一去你们那儿气压就特低,都不敢说话了。
那种气氛就是:我们和普通班是显然不同的,所以一般跟普通班也玩不到一块儿。
我们班有一个显著特征是——没有绝对的第一名。
竞争太激烈了。你长大那个环境,如果你足够出色,肯定是班里第一名,因为其他竞争的人都太弱了,但是在我们那,你这次考好了,可能进前5,下次发挥不好,就可能垫底。所有人都很厉害,于是始终有一种紧张的氛围在。
有些同学明显的家境很好,文具盒崭新崭新,里面是成套的香味橡皮、转笔刀、尺子,和我们平常用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还有同学爸爸是开电脑公司的,或者很高的领导。我能感觉到那种明显的阶层差别。
实验班依然采用淘汰制。9班学得不好会淘汰到8班,8班学得不好会淘汰到普通班。然后每年会从普通班选拔一部分好学生到8班,再从8班选拔最好的到9班。
还有一件事给人非常大的压力,但你没有办法抵抗——
每次期中、期末考试,学校都会写一个非常大的榜,贴在走廊里,一下就能看到自己排在多少名。
对我来说,那种耻辱感非常强。
我进实验班的时候,第一次考试,是第21名。没想到这就成了我整个初中的最好名次。后来每次都考差一点,最差的时候好像考到倒数第三还是倒数第五,大概就是55个人我考到了第51或者53名。
老师每次就说:“你们这些后面的差生都给我留意,到时候淘汰你们,别怎么着……”都是这种威胁式的。
老师的意思肯定是让你要努力,但那种很高压的状态,并不能让我产生努力的动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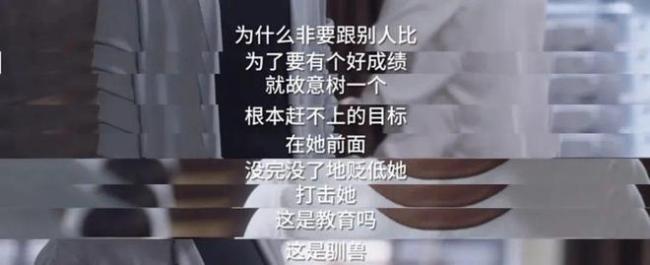
班里有好几个英语很好的人,他们课内根本不用学,因为他们在其他场合已经学会了。在那种环境里,始终有人比你强,你不知道你在跟什么对抗。
你不知道到底怎么才能够在这个环境里获得一点自信,我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有信心说“我是一个挺不错的人”。
每学期开学一般都是最开心的,然后发现上学期积攒的听不懂的,这学期也继续听不懂,然后就玩,到期中考试的时候开始慌了,等到期末考试要来了,感觉每天去学校就像走在通往古罗马斗兽场的路上……就要和我的“塑料姐妹花”朋友捉对厮杀了。
如果我要是“杀”过了她,她就会突然不理我,下课不跟我结伴上厕所了。我要没“杀”过她,我就可能被淘汰到普通班……真的,在想的都是这种事儿,每天处于一种惶惶的状态。
那会儿不流行说牛人,流行说牲口,谁学习好谁就是一个大牲口。
普通班的人平时会把实验班的当作怪物。万一我被淘汰下去,我该怎么跟他们相处?就是那种巨大的焦虑。
四、心理健康课解决不了学生的心理问题
因为生病的是那个环境
同学之间的气氛,也很微妙。
白天大家都在那疯玩,下课后男生一个把另一个摁地下,玩得一身土、一头汗,但是晚上都自己偷偷学习到很晚,还不能告诉别人。
我听说,有女生让父母给自己讲昨天晚上电视剧的情节,以便第二天在学校里大声说:“啊?你都没看那什么什么电视剧吗?昨天演的什么什么……”
我也遇到过不止一次,我在那看书,然后我的塑料姐妹花好友走过来,把书给我合上说:“别看了,就知道傻学!走,咱们玩儿去。”但当我考试排名比她高的时候,她突然就不理我了。下次如果她考得比我好,她又像没事儿人一样热络。
还有一个女朋友有一次考了第一名,很多之前根本不理她的人下课都围到她身边,把她纳入自己的圈子。
感觉实验班里排名前10的人不会跟排名20的人玩,排名20的也不会理排名30的。在那个环境里到底怎么自处,是一件很让人困惑的事。
我会纳闷,为什么那谁谁谁,平时没见他/她学习,他/她怎么考那么好?也会慢慢说服自己:有些人就是擅长学习,而我就是不擅长学习,然后就会怀疑自己,会自卑。
我爸妈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让我变好,他们只知道说:“你小时候可乖了,结果你一上中学就不乖了。你小时候学习可好了,你刚考上人大附中实验班的时候,全班排21,结果名次每回都往下掉……”
就会这样数落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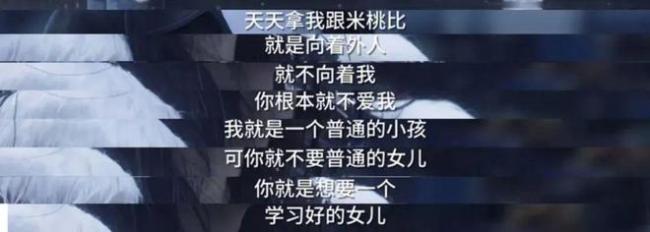
当年有一个男生我很佩服他,不管别人怎么干扰他,他都会不以为然地一笑,然后自己该干嘛干嘛。比方有人过来拍他书说:你看什么呢,有什么可看的?他就只是抬抬头,看人一眼,然后低下头继续干自己的事儿。我当时觉得那男生定力很强,很了不起。
但是没想到,他考上中山大学以后,在大三时自杀了。
我们初中两个实验班的同学,读大学后有两个人自杀,9班一个,8班一个。9班那个上的是北大化学系。
其实人大附当年已经开设了心理健康课,意识算很超前的。
但那种心理健康课,它不能改变当时的教学环境,所以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。就好像为了避免你生病,我给了你一种药,但实际上生病的是那个体系、那个环境。
我觉得那个环境是逼人早熟的,有点像一个加速器,要求你赶快定位自己、想办法提升自己。
它不会教你要怎么去提升自己,而是——我就告诉你,你和我的标准有多大差距。
是因为我个性比较敏感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吗?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有这种感受。
那些排名前20的同学可能会有高手过招的快感,但如果你不是,也很可能觉得压抑。
五、高考没考上第一志愿
我还挺开心的
初中升高中,实验班很多人不用考试就直接升入本校。但我属于要考试的那部分人,我考上了,被分到了普通班。
普通班的气氛要比实验班正常得多。没有淘汰制,老师也管得比较松。
当时我们班物理老师、政治老师讲课都特别烂,就照着课本念。后来只要物理老师上课,我就躲到厕所去,捧本闲书自己看,等到下课了我再回去。
高中时有一些同学家里挺有背景,知道自己会出国,学校也是睁只眼闭只眼,管得没那么死。所以翘课也没人管我。
2021年得了金球奖、奥斯卡最佳导演的赵婷,就是我在人大附中时的同学,同届不同班。初中时她在普通班,是少数几个我打过交道的普通班的朋友。
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宋丹丹是她后妈,她爸当过首钢总经理。我最早听到迈克尔·杰克逊的音乐就是从她那里,因为她有随声听,有时候我们会带着耳机一起听。
 赵婷
赵婷
她高二就去英国读书了,后来又去了美国。人大附中像她这样家庭背景的人不少。
这种重点中学,学生构成是很复杂的,会让你很早就意识到“不公平”。
那时候我就对考分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件事,感到特别怀疑。再加上高中开始听摇滚乐,我变得越来越叛逆。
那三年我基本没怎么学习,就是在图书馆看了三年闲书,金庸、古龙、卫斯理、周立波、张贤亮……各种小说。
我从小也比较喜欢看文学类的东西,那时候又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出口。
刚好我妈允许我每个月买多少钱的书,专款专用,我就经常去海淀图书城买《科幻世界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音乐天堂》,淘打口带。

那时喜欢的Radiohead乐队专辑
我给摇滚乐杂志写信,发表在编读往来栏目,于是收到全国各地很多来信,结识了一些有共同爱好的笔友。大家资源都有限,会互相寄自己喜欢的磁带,交换来听。那种友谊非常纯粹,跟我初中时在实验班经历的截然不同。
从实验班出来以后,班上有很多不好好学习的人,他们有些可能是和我一样,产生了一些疑问,在这疑问里,我们在探索。有人通过听摇滚来释放,也有人在谈恋爱里释放,还有跟我一样看小说的。
大家都想看看,有没有别的路可走。因为学校没有给我们答案,所以我们自己试图找到答案。
高三时我从理科班转到了文科班,心里隐隐觉得自己想做记者。
到了文科班,我数学能排20名左右。虽然不怎么学习,成绩也没有多差,完全在靠数学和英语往上拉分。政治、历史我都拒绝背,应该考得很低,最后高考出分,上了首都师范大学。
我爸妈对这样的高考成绩肯定不满意。他们老对我有不切实际的幻想,觉得你都能考上人大附,那你就应该能考上清、北。
只不过,我用我的行动一点点把他们的预期给拉低了,最后拉低到他们不同意也没办法。
直到高考填志愿,我妈还希望我能按她理想的路径走,她一定要让我读会计,我也听了她的,第一志愿报的首都经贸大学会计系。结果分不够,没考上,进了首师大。
我还挺开心的,没考上挺开心。
六、小初高的生活脱离“真实世界”
进入大学后我开始“叛逆”
大学里,我彻底脱离了父母期待的路径。组乐队,排话剧,做社会调查,过得特别充实。我很享受我的大学四年,感觉把中学时的压抑都找补回来了。
回想起来,从小学到高中毕业,我的生活跟“真实世界”好像不发生什么关系。
大人告诉你,你的目标就是拼命学,考清北,但是上清北是为了什么?我不知道。
学校里教你要真善美,但为什么你掏心掏肺的朋友,会因为一次考试成绩就改变对你的态度?为什么有人中考比你低30分,还是一样有办法上人大附的高中?
你隐隐会察觉到那些言不符实,那些灰色地带。
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对世界的批判,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。
我喜欢的音乐也是那种开创性质的,就像“曾经人们都是这样循规蹈矩,但我用一种新的方式打开了一个局面”。有创造力、有生命力的东西特别吸引我,哪怕现在,摇滚乐里强调的那些价值仍然是我所认同的:爱与和平,世界大同,要做爱不要作战。
对,我觉得这些没有变过。
这就很容易理解,为什么我上大学时会跟A君在一起。
A君大我三岁,没有上过大学,之前在西北老家做乐队。那时候全中国玩摇滚乐的人都会来北京找机会,他也是。
一个朋友介绍我们认识。他当时是进了一个临时项目,帮人家做音频后期。我觉得他特别有那种野生的生命力,人也挺聪明,自学能力很强。我们聊音乐很能聊到一起去,身上也都有反叛的底色。
A君吸引我,很大原因是:
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连墙都没出过的大学生,只在OICQ上跟老外聊过几句“我喜欢哪个乐队,你喜欢哪个”……但A君是真搞这个的,他知道组一个乐队最必要的是什么,需要什么样的人,怎么才能出得来。他直接在那个圈子里,肯定比我光聊聊要有吸引力。

90年代末,很多外地来京的摇滚乐手住在树村。
他跟人在通州合租了个房子,很穷,每天就自己关在家里做电子音乐。我们谈恋爱以后,赚钱支持他的音乐事业变成我一个不小的负担。
我记得上大学时我就经常要操心他的房租、水电费。
我爸妈极力反对我们在一起。但这段感情我还是深陷其中,来回牵扯了八九年。
这里面确实有一种自始至终的反叛。
特别是当我爸妈给我压力说“你必须要跟他分手”的时候,我就偏要跟他在一块给你看。好像越是全世界跟我作对,我就越觉得自己坚持的东西是有道理的。
现在想想,与其说我真的觉得和A君特别合适,不如说我特别想跟以前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,想脱离那种被父母管理,被父母规划、认可的人生。
记得我大学实习时,我爸把我塞到他单位的进出口部,每天的工作就是填外汇单,然后去银行,把外汇单递给窗口的人,然后给植物浇水,擦桌子、扫地。一天就结束了。
我特别暴躁,觉得我干不了这个活,我实在不想过那种生活。某种程度上,我是在选择有意识地避开那种生活方式。
我那会儿也确实相信,和A君在一起的生活里才有我在追寻的某种东西。
七、30年后,我不想做传奇故事的主人公
也不打算加入“鸡娃”大潮
大学毕业后,我做过画廊经理,也进过大厂工作。在我收入已经很稳定的时候,A君的音乐事业依然没有进入正轨。
我们之间的力量、关系都开始发生变化。
最后分手,是我自己的思维转变了。
我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复杂了。我意识到,只是喊一些口号是没用的。
我不想做一个传奇故事的主人公,也发现——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生,也是有意义的。
从15岁开始,我一路叛逆,一直叛逆到了快30岁。经历了长达十几年,我才领悟到,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加弥合的方式,去考虑人生中的种种问题。或许我以前走得太远了。

30岁之后,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先生。他同样心怀很多理想的期待,但又脚踏实地,在积极地做着很具体很真实的工作。我们有很多精神共鸣,而他所处的行业和工作,也刚好符合我父母的主流预期。
直到我进入了这段新的关系,我和父母之间长达十年的紧张才渐渐缓合。
现在,我也成为了母亲,我的双胞胎孩子也到了上学的年龄。
去年,离开海淀多年的我,又举家搬回了海淀。孩子用我爸妈老房子的户口,入读了海淀区的普通小学。我们之前住的昌平,基础教育还是太薄弱了。
我并不打算加入越来越卷的“鸡娃”大潮,也没有给孩子报奥数班。那条路我已经走过了,不希望孩子再重复一遍。
我觉得只要家长不把注意力放在太过功利的目的上,好的教育还是有可能发生的。
我时刻提醒自己这一点,不要去控制孩子,往长远了看,孩子人生中很多关键的选择,其实是父母左右不了的。
想起我妈以前老说:你就是不好好学,不把心思放在正事儿上,你如果高中不是整天看闲书、听摇滚,绝对也有机会上清北!
她不明白的是,如果我当时不这样做,说不定早就抑郁了。至少我自己还有一种解决方式,用它解决了我精神上的困境。
有些痛感,是父母无从理解,无从体会的。
成长,也终究是我们要独自承担的事。

这是一篇私人回忆,是完全个人的讲述声音。它可能片面,不能代表全貌,肯定也有很多跟小巫升学路径相似的人,对这条路有完全不同的感受、体会。
但对一所名校的实验班来说,“失败者”的声音是稀缺的。不用多久,一定会传来多少人考入清北的捷报,满屏充斥对胜利者的祝福——
这时候我想,也需要有另一种声音,拼图才完整。